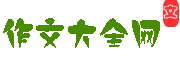脚板踏上那铺满苔藓的泥土小道,酥酥的,软软的,是泥土的气息。还有那砌得整整齐齐的泥墙壁,用手扶上去,却突然发现它早已变得坑坑洼洼的。惨灰色的一片,只有那在风中无助摇曳着的小红绳,孤伶伶地挂在墙沿上,像一声声秋风吹落的叹息,在我心中不住地回旋……
老人坐在破旧的藤椅上,出神地望着朝阳升起,夕阳落下,空洞的眼,如盲人一般没有焦点。
他是我爷爷,我是他最爱的孙女……
算不上健壮的身躯总爱倚着那残旧的藤椅,那是一把上了年纪的藤椅,没有华丽的雕刻,没有鲜艳的颜色,一切都显得它是多么的朴实无华,而它——是爷爷亲手做的第一张椅子。
爷爷是一个木工,这辈子都活在木头的沉寂里,多少作品随着时间的消逝,最终都如尘土般变得无用,碍事,唯独这张藤椅,陪伴了爷爷大半个人生。
爷爷又望着那轮渐渐被地平线遮蔽的红日悄悄地走神,那条地平线把一切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把爷爷身后的悲凉映得如此无力。
“欣啊,你妈有把两只金戒指给你看过吗?”说到这事,爷爷浑浊的眼珠总算镶上了点光彩,带着期待等待我的回答。
“没有啊。”我应付式的话语在静谧的夕阳下显得如此的不在乎。
“是吗?”爷爷眼中的光彩再一次熄灭,嚅动了一下嘴唇,便不再出声了。
就在我抬头的瞬间,眼光触到爷爷枯井般的眼睛,心底不禁泛起心酸的痛楚,讪讪地笑着说:“怎么会有两只金戒指呢?”
爷爷再次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像倾诉秘密般靠近我的耳朵,神秘地,孩子气地说:“我帮你和你姐都打了一只金戒指,可漂亮了!你妈怎么不告诉你啊。”爷爷用沧桑的嗓音描述着戒指的形状大小,用颤抖的手指在空中比划着,肌肉松弛的两颊由于激动浮上淡淡的红晕,沉醉在自己的想象里。
我略显惊讶,然后好笑地摸摸鼻子:&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