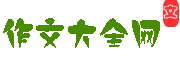的心灵里体验到了世界上除了爱,还有恨;体验到了一种平白无故的委屈、一种不甘受侮的抗争。当然,祖母不会放过我,她手里拿一杆戒尺,要打我的手心,我不让她打着,从楼上跑到楼下,从楼下跑到天井里,从天井里跑到家门前的石板路上,跑到后门的河滩边。她小脚伶仃,哪能追到我呢!母亲当着祖母的面大声地呵斥我,但母亲分明只是为了维护祖母的那点“面子”,那声调,那语气,都是在护着我的。这样地“对立”了一段时间,我就再也不到祖母的房间里去,也不再叫她;她也就不理睬我。吃饭时,母亲在一个小碟里给我另盛一点菜,把饭和菜放在一张方凳上,我自己坐在小椅子上慢慢地吃,倒也安然无事。但她对我们孤儿寡母更加没有好气。对我奈何不得,就把气撒到性情温和不爱惹事的母亲身上。不是嫌母亲做的针线活不好,就是说母亲干活太慢,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母亲越是忍受,她就越是厉害。母亲在屋里暗暗地流泪,我搂着母亲,像个大人似的说:“她骂你,你也骂她。她凶,你也凶。不用怕。”可是母亲说,祖父、父亲都故去了,哥哥们在上学,我还不懂事,暂时还只得在这个家里,靠祖父留下的产业过日子,只能是忍着点。庭院深深,度日如年。
过完四周岁生日,又一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早晨,喝过糖末花茶,要向长辈拜年。读过几年私塾的母亲深受父亲的思想影响,她不让我跪地叩头,而是深深地鞠一个躬。她说儿女不忘父母养育的不易,读书,争气,就好。我向母亲鞠躬以后,正迟疑地走向祖母,一抬头,又见一双白眼,于是转过身就走。因为是过新年,祖母不好发作,对着母亲说了声:“没有家教。”自己上楼去了。自此以后,我已决然地不把祖母看做是我的祖母。我每次见到她,昂起头,唱着自己也弄不清楚的歌儿,一直唱到看不见她的身影。这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得胜的喜悦,只是难为了母亲。
这年春天,姨母与姨父从南京回来,姨父身体不好,回老家来休养。他们听说了祖母对我的“压迫”与我的“不屈”,就邀母亲和我去与他们同住。姨父对我说:“你父亲留学日本,学习纺织工业,主张科学救国。他一向主张男女平等,希望有个女儿。你要读书,让你的祖母看到你这个遗腹女怎样地有出息。”于是,姨父为我起个以后上学的名字:锦贻。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