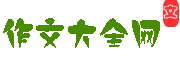房间,自由却堆积在无尽的囚笼中央,两眼空洞的漠视着窗外的白色人间。我向往的世界,一切的一切全是白色,雪白的颜色,天空,树上,地上。全挂着雪灿灿的白颜色,白得刺眼夺目,天上还在飘的,地上已停滞的,丝丝缕缕像钻到土壤里一样,钻到我的心里。
我喜欢,所以才会答应自己,失手让它离去。
我竟然眼睁睁的看着我最心爱的伙伴离我而去,挥手道别的时候,天下着雪,不愿意离开我眷恋着的温暖的口袋,后来等她彻底离去后,我发现我有的时间去揣在冰凉的口袋里,去依偎温暖的记忆,欲寄出去的道歉信加慰问信,塞满了整个破抽屉,一把老式钻孔下拉小铁锁,隔断了我们的牵连,后来钥匙被弄断了,索性就连着抽屉一起丢了出去,换了一个红木制作的推拉式高脚床柜给我,我整天就呆呆的看着那个木柜,母亲把它擦了又擦。我说,给我上个锁吧。她定定的放下手中的活,莫名其妙的怪异的看着我,转过头来却对父亲说,这孩子,有啥秘密非要锁着呢,这样不是多好,上锁多不好看啊。反正之后,那个柜子就一直没摆东西,母亲就乐颠颠的把它抱走了,从次,我压抑空白的房间里,又腾出一块空荡荡的小空间了,我甚至有时候还会呆呆的看着那个角落,眼睛一花,就仿佛又能看到那个装满赎罪用的柜子。
第二年,有位喜爱仿古的富人家看上了我们家的红木,愿出原本价钱的十倍收购,母亲大喜。
除夕晚饭的时候,我无力的托起筷子,咽在喉咙里的白米饭,就硬生生的哽咽的卡在了中央,平淡无味的阻咽了细小柔弱的脖子,我艰难的咽了咽,刺得一眼泪水同时飙出来。口中呜呜直作响。母亲漠然的看了我一眼,给我舀了一点残羹剩汤,说吃个白米饭都会噎着,真是倒霉。父亲一言不发的把头埋得低低的,不停的往口里扒饭。浓渣的胡须被牵扯得有力来回蠕动。遒劲枯槁像树根似得的手指,摇摇摆摆的支撑起两个木棍,穿插在粒粒分明晶莹饱满的白米饭里。半响,他抬起苍老布满皱纹的焦黄脸庞,“卖了也好,反正没多大用途,摆在我寒酸四壁的家中,也不像样,换得的钱也刚好可以购置一些有实用的东西”
一手正端着勺子,里面盛着浑浊的菜汤,一顿。劈哩啪啦全部跌落,剩汤蔓延在古朴的四角方桌,然后顺着我这边滴落了下来,我惶惶的不安急躁起来,一边拼命的摇头,一边口中呜呜的配合着手势,告诉着我的想法与观念。母亲瞧都没瞧我一眼,毫不犹豫的就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