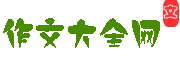日子是一段伟大到无法逾越的微弱距离。
——题记
那天,我是第一次下乡,到我那祖祖辈辈曾生活过的地方。
车子一路颠簸地开,像在海中远帆的船。我抱着个袋子不停地吐。有时抬起头,看见金色的麦海。有正在农活的农民们瞧见了我们的车,像是发现了金子般指指点点,旁边的牛“哞哞”的叫着,十分欢愉。
这里是一片天堂。
行至半路,车子暴了胎,只能步行。打开车门,一片荒芜与萧瑟。
习惯了城市的糜烂与喧嚣,突然来到这阒静的地方,茫然无措的只能站着。天空明净的涌出了水,风中混着先祖圣洁的气息,熟悉而又陌生。
我出生后不久,父亲边带我离开了这儿,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的出生地,可记忆却不曾给这落后的地方一席之地。
面前是一座破败的屋子。肮脏,陈旧。里面几乎什么也没有,只剩一朽木桌立在那儿,腐坏到了极致,霉菌已侵蚀了它的五脏六腑。也许是经年的雨水,白色的四壁已浸透了水渍,一圈一圈,荡漾出老屋的落寞。
父亲说这时他生活过的屋子,一丝小小的痛苦划过父亲有些发福的脸。
那一瞬,我忽然发现这里是天堂,却是天堂的崖边,灼热的气焰从那黑暗的深渊蔓延而出。
老屋旁住着另一户人家,是个花甲老婆婆。她见我们来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的变化,一双眼睛空洞而又麻木。她手里捏着一枪烟杆,时不时地向里加些黑色的烟屑。
里屋传来莫名的声响,我因为好奇便向里张望。一只干瘪的老鼠踉跄地爬着。
“别看了,老鼠而已。”老婆婆的声音如同冰霜般尖锐地划过耳膜。她的话那么简单。是习惯了老鼠吧,亦或是些别的什么?
我想老婆婆也曾是个闺秀,她加烟屑时的兰花指如此特别,叫人心疼。但也许从她出嫁的那一刻起,梦的齿轮便也丧失了活力,生了锈,老的已承载不起远航的希望。于是只能用这千尺黄土垒起一座孤坟,埋葬了遥远的闺阁梦,每天来凭吊。
黑色无望的坟头上已经长满了杂乱妖娆的罂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