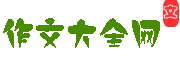子管什么呢?”
我的性格极像母亲——不到黄河心不死——根本不会因为环境的压迫而改变初衷。我鼓起勇气,趁着雨大消些霸气之声的时候,继续追问:“到底去哪里呀?我一个人在家,你放心的呀?”
父亲从小对我就不那么的看好——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别样的教育,当年爷爷也是拿这招来教父亲的——此时,更是怒不可竭,斥责道:“你屁股是硬了吗?再问的话,我给你一棒子头。”
我是经不起摧残的花,但却是经得起摧残后重新绽放的苞。于是,我毫无节制地乱叫,像是疯了得狮子,更像是犯了毒瘾的烟鬼,一副无赖之状,直映父亲的眼底。
父亲是个君子。君子最怕被小人给黏住,不过,在除上帝以外,别无佐证之人外,君子也可以暂时放下身段,做一回小人。这自然是兵法所云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这一顿打是逃不过了。
情愫到了极点的时候,就算是黑白无常来锁魂,也是无济于事的。这是父亲生前常和我说的话。
我一把拉住自行车的后座。父亲起初硬骑,由于我年纪小,经不住这力道,便一个跟斗侧倒在旁了。父亲不忍,就下车将我扶起。可小人之心君子又哪能真知道呢?我索性愈演愈烈,说手肘撞石,脚踝碰砖。父亲慌了,赶忙给我换了湿衣服,将我携至车杠上,往医院骑去。
我躲在车衣里——只能看地,不能远眺,我只能凭着记忆来判断车至何处了。雨似乎更大了,点点滴滴都溅起无数小水滴。弯道儿一个个的过,我的心也似乎一阵阵的受刺,颇不宁静。
我把弄着父亲的手腕,又抽咽地说:“爸爸,对不起,我骗了你?”
父亲丝毫没有减速的样子,但又有了停车的欲望。
“文辉啊,你的心为父怎么不知道呢?请你记住,这是你第一次乘爸爸的自行车……”
我终于被父亲带着走了。后来去了哪里,我依稀不见了。
时间转瞬即逝,年轮也从不饶人。我站在阳光明媚的春日下,闭目养神,对着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