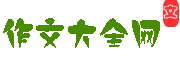我曾看见过一张照片,那是一幅藏东南的原始森林的照片,视野所及之处全是高耸的林木,上面盘缠着奇形怪状的攀援植物;许多植物的根暴露于土壤之上,交错纠结,一路崎岖地伸向不知名的远方。或许从天空俯视,这片原始森林就像山的一件华美葱茏的袍服;而只有身处拍摄者的位置才能觉到自身的渺小不可及,蓊郁的树冠几乎遮住了所有的阳光,底下暗无天日,似乎披着了一层暗墨色,表面静默;而在阴晦中,你看不见那其中的一个个细胞,正努力生长,冲破黑暗,刺向云霄。
我惊叹于这大自然的手笔。历经千百万年它依然耸立,巍峨不可动摇,维系了一方水土,存在了许久,许久。
或许这种景象我只能透过杂志的彩照尽情想象了。只有亲身涉足过的人们,才有资格述说原始森林在眼前是无法颠覆的伟岸和深邃,穿越时空绮丽的伟岸和深邃。归来后,便是曾经沧海。
而有另一种意象又不同。如果说原始森林是金戈铁马,那么她就是绿水人家;如果说原始森林是少数民族粗犷的音调、黄土高坡上刮过的信天游,那么她便是妩媚柔软的吴侬软语、吴越地区流传的黄梅戏。在气势上,她永远比不过那占有了亘古时空的原始丛林。她,便是江南的林。
江南的一切似乎都是婉约的,仿佛都锁于了“杏花春雨”,仿佛都锁于了“小桥流水人家”的粉墙黛瓦,锁于了细雨朦胧中油纸伞下的一缕芬芳。而在温润的日子里,那一打慵懒的阳光,轻柔地铺下一层树荫,从困倦我曾看见过一张照片,那是一幅藏东南的原始森林的照片,视野所及之处全是高耸的林木,上面盘缠着奇形怪状的攀援植物;许多植物的根暴露于土壤之上,交错纠结,一路崎岖地伸向不知名的远方。或许从天空俯视,这片原始森林就像山的一件华美葱茏的袍服;而只有身处拍摄者的位置才能觉到自身的渺小不可及,蓊郁的树冠几乎遮住了所有的阳光,底下暗无天日,似乎披着了一层暗墨色,表面静默;而在阴晦中,你看不见那其中的一个个细胞,正努力生长,冲破黑暗,刺向云霄。
我惊叹于这大自然的手笔。历经千百万年它依然耸立,巍峨不可动摇,维系了一方水土,存在了许久,许久。
或许这种景象我只能透过杂志的彩照尽情想象了。只有亲身涉足过的人们,才有资格述说原始森林在眼前是无法颠覆的伟岸和深邃,穿越时空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