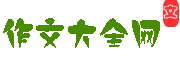,殊不知距离是最锋利的刀,轻易割断情感的脉络。
直至那日,我刚替他沏上一杯茶,他说“兰卿,我,要成亲了,十日之后,娶得是秦府小姐——罗敷。”我端茶的手微微抖动,滚烫的茶水洒在手心,但我并未感到烫。只觉得手背上有泪水划过,热得灼人。胸膛里似有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他连忙起身,问:“兰卿,怎么了?”我勉强扯扯嘴角,露出一个大概是我生平最难看的笑容,说:“没什么,风沙大罢了。我真的很高兴,因为-----因为我们是知己。”“兰卿,相信我,你一定会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夫君。”会吗?如果没有仲卿,兰芝的存在又有何意义?望向窗外,太阳正缓缓下坠,像茶杯上挂着的一枚蛋黄,缓缓滑落,一直往下坠,缓慢地,无可逆转地沉沦,迷离的阳光中,太阳正吞噬最后一缕斜晖,时方盛夏,我的身上却只有冰冷的寒意。
成亲前一日,他酩酊大醉,在我房外敲门,一声一声就像扣在我的心上,我抵在门上,紧咬着唇,不去开门,我怕见他,更怕见了不知如何是好。敲门声止,耳边传来他低沉的嗓音:“兰卿,我知道你的心意,可我真的不能接受。有时我会觉得,你就好像是她。你的眼神,你弹箜篌的样子,真的很像,有时我甚至不敢看你的双眼。我一直在等一个人的出现,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她为我等了那么久,我不能辜负她,所以,兰卿,对不起。”那声音好似冉冉升起的一缕云烟,扶摇直上,穿过屋顶和墙壁,传入耳中。我听到了他沉重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打开门,院内早无人影,唯见那深蓝的如墨的天上有一钩月,低得像是触手可得。衬着薄薄几缕淡云,月色清寒,颜色暗得几近赤色,望去,就像铜镜上的胭脂痕,洇然就要化开了一样。月下彷徨,却不复当年模样,晓风伴银钩,影乱难拼凑。残月倚寒楼,凉风袭衣袖,怅然抚窗棂,欲说语又休。一阵清风吹过,面上冰冰凉凉,才知已然泪流。
第二日,我来到他家中。看着府内触目可及的红色,我只觉刺眼。我见过罗敷,只因她长相与我前世肖似。今晨,我精心梳妆打扮了一番,穿上与前世式样相同的夹裙,脚上着绣着兰草的绣鞋,腰间的带子像流水般轻盈地晃动着,涂上淡雅的胭脂,带上琉璃耳坠,勾画出黛色眉峰,面若桃花,顾盼神飞。我打断了他的拜堂,她的母亲怒着问我是何人,那神情让我想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