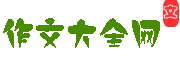远方的爸爸:
我想打电话听听你的声音,但我突然想起家里没有电话。
我不得不在这昏暗的月光下提笔给你写信。
你,匆匆地出现,匆匆地言语,匆匆地消失在我的地平线。
但你的爱从未匆匆过。
此刻,我又想起了往事。我的出生,似乎就给这个家带来了数不尽的苦恼。我有个哥哥,母亲还想再生一个男孩,但却得了我这个“不出息”的女娃。那时,爷爷就坐在椅子上叹着气对妈说:“你的肚子咋就这么不争气?”后来我就一直看到妈妈一个人偷偷躲在屋里抹眼泪。
我到了该上学的年月。你就跟爷爷商量说,我是不是该上学了?爷爷硬生生地抛出一句:“一个女娃,要上学干啥,再说老大已经上学了,我们哪供得起两个娃呀?帮着下田干活吧。”
那晚,我看到你坐在油灯下,扳着手指算学费,又无奈地摇了摇头……就那样在冰凉的椅子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我帮着二叔一起去割稻。酷烈的炎阳照得我皮肤生疼,汗贴着头发流,蜇得难受。突然远远地看到一个一瘸一拐的身影――我纳闷,这年月怎会有人不忙着收割,反倒在闲逛。
累了一天,皮肤被晒得赤红,衣衫被汗水浸泡得紧贴着身体。到家时是你开的门,我一愣,才知道,原来那个人就是你。你故作轻松地笑了笑,又拄着一根木杖转头进屋了。我进屋看到了母亲,她两眼里充满着血丝,又红又肿。我的心提了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是母亲告诉我的,她一边抽噎着一边说:“你爹为了替你筹学费,今儿天没亮,走了几十里路去镇上拾荒。本已捡了不少东西,但他做什么孽啊……”,母亲抹了一把泪又继续说,“去捡了一个大户人家扔下的废花瓶,被人瞅见了,一大帮拾荒的便过来把你爹打了一顿……他们便拿了那花瓶径自卖了去。天理何在哪!”你在一旁低头不语,忽然抬头说:“不早了,我做饭去。”
母亲一把拉住了你,“逞什么能啊,坐下。”母亲便帮你敷药,那腿上被打得皮开肉绽,血里还掺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