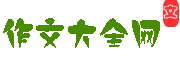在那个让人看不见找不到的地方。我抱着“我”,走在一个楼道里,楼道的两旁有很多房间,但都紧闭这门,那里我可以闻见刺鼻的消毒水味,我知道自己在医院里,但我却不知道我为何要来到医院。我只感觉自己很累,我很想随意的进一个房间,躺在一个床上安静的睡下或者在楼道的地上睡下,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还是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前走,我也不知为何要这样做,也不知道楼道的尽头是什么在等待着我,只是让我感到无尽的恐惧,我似乎不能停留,只能往前走,怀中的“我”,那样轻,似乎没有重量,可我还是那样累,那个“我”,轻得只要一阵清风并可以离开我的怀抱,但我并不想要“我”离开,我只剩下那少的可怜的真,没有了,我便一无所有。我还是走到楼道的尽头,可我并不知道尽头是什么,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仿佛在下坠,当我的身下开出了一朵花,那朵花并不是像我喜爱的百合一样洁白,而是鲜红的,红的刺眼。我想要挣扎,因为我弄丢了那个“我”,张口欲说,还没说出声,便失去了意识。我耳旁的流言蜚语是听到了——“这孩子才十七岁哎,哎呦,搞什么啦,”“哈哈,你不知道呀,听说是干那个的呀,一个晚上才一百块,”“对呀,对呀,这种贱人,死了活该哟”“就是就是,没娘教的孩子,”“晦气晦气,起她远点吧”“哎呦,我听说他还有个弟弟呢,长得很是英俊嘛,不过好像得了癌症哦,活不长咯,嘿嘿,以后离他远点吧”我对这些流言蜚语已经成了习惯,在我失去意识的前一秒,我想说的是:晨晨,带我去一个长满百合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木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一个可怕的噩梦,也许那并不是我做的梦,也许是我幻想出来的。我也曾怀疑过我得了幻想症,我迷失了自己,我甚至自己踏上了迷途,谁可以将我救赎。没有了。
直至去年十二月的中旬,我将最后剩的可怜的真,放在了一个男孩的身上,可在今年八月的中信,着心中剩下的真,也残忍的耗尽了,没有任何征兆,就这样随风逝去。
以后的我会怎样,我并不知道,我的未来是怎样的,我也不知道。
我想大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