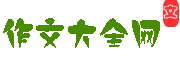着姑母。我试着张了张嘴,最简单的音节一传到空气,就散了。把手死死攥紧,指甲狠狠抠进肉里,哪怕我开口也说不了话!说不了!
父亲来了,他每一个步伐都是哆嗦的,蹒跚的,“庄洁?庄洁!庄洁……我们,回家吧……回家啊,不用怕……”我鼻子一酸,紧紧抱着父亲,用力点头。我说不了什么,无法发出动听的音节,父亲听不见什么,只能感受自然的律动。此刻,单是拥抱,附近的空气都能融了,化作无声的光芒,倾泻,流淌。
毕业后,我随父亲下乡,卖点烟草什么的小玩意。
经常记起逝去的母亲,比我小一岁的妹妹。她们都在我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妹妹出生后母亲因难产去世,别人都说是她克死了母亲。父亲也这么觉得,而且家里也没几个钱,最后丢弃了她。连名字都没取。
想过很多次,如果她们中的一个回来,我都会双手奉上春季般的温暖和欢跃。
哪怕有过罪孽,浑身淤泥。
郁青——
几年后。
我坐在车上,远望见一辆巴士在巷口静下,面无表情的人一步步挪下车,他们各奔东西,只有回到家,积蓄的笑脸才用力献给家人。家人?我想至这,脸上略微抽搐了一下。大概是山上冷的让人发怵吧。
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外,我停住,拿起一张纸校对门牌号时,从窗口感受到里面暗黄的灯光,那束不大亮的光透着门缝,洒在我每一缕乌黑长发上,连发梢都被照暖。暖?呵,也许这种感觉便是了吧。
感受到屋外的动静,屋内的人开了门,木门发出“吱呀呀”声,温丝丝的空气一涌而出。久违的气息满溢,像是我长住过的地方似的。
开门的男人盯着我目瞪口呆,或许觉得我和庄洁长的相像吧,考试那天也有人说过。
庄洁,原来我对不起的人是你。
后来,我时常想,这世间还有亲人总是带着温情的。
庄洁——
一直想找回妹妹,找了些过去的同学帮忙。忙活了这么些年,总算有了大致下落——全在这份档案袋里。
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