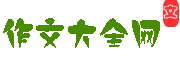打我记事儿起,爷爷家就总爱养猫。
很小的时候,我一到爷爷家,便一个屋一个屋地找一只雪白的猫咪,还记的那时它最爱呆的地方就是一间破旧的小屋,它总会卧在一大堆堆在破床上的很旧很旧的东西的最项端,这使我着了不知多少次急——叫它它不应声,捉它又捉不到,只能好说歹说似地唤着它,“咪咪,咪咪……”。
一旦什么时候我回家,它没在那高地方,正好在地下卧着,我便开怀了,蹲下来一遍又遍地轻轻抚它的绒毛,乐此不疲。
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经常在它身上采用自己独创的逗猫法,并且不知多少次,看着它团团转的样子,我银铃般的笑声在院子中回荡。具体地逗猫法是这样:爷爷家在农村,有很多很早以前的小木櫈,长方形的凳面,四个腿之间都有根横木棍互相固定着,高度大约比猫咪高出一拳,大都为砖红色。于是,我便会在猫咪睡觉时,偷偷地把一个小凳子放在它身上,但要保证任何部分都不碰着它,让它置身于其中,然后在这个木凳的四周和上面再加木凳,摆成各种样式,通常像个城堡,很壮观。之后我便坐在一边,静侯猫咪的醒来。
直到猫咪努力地睁开了自己朦胧的双眼,它才会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奇形怪状、四通八达的“建筑物”当中,此时我便来劲了,看着它走来走去,上去下来,就是走不出去,我还会幸灾乐祸的说上一句:“咪咪,别走了,这就是你的家呀!”等到它实在难受,极其想出来时,我才会一点点地解除对她的“封锁线”,然后看着它看我像看救命恩人的眼神,心里那个乐呀!
后来,她还生了一窝小猫——还在那个老地方,可大都死去了,只活下一只公猫来。再后来,它便不见了,到底是“离家出走”还是“客死他乡”,都无从知晓了。
于是,我便经常与那只刚出生的小猫玩耍,还给他起了名字:“花花”。有些俗,不错,不过猫的名字嘛,叫得顺口就行。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猫咪很喜欢会动的小东西,于是灵机一动,找来一个瓶盖打孔,然后把长绳穿进去,这样只要我拉着绳子的别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