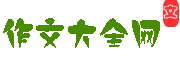毫无征兆的在某个冬天里把春天瓦解了。那些春回大地鸟语花香的感觉完全消失了,就像是渗入泥土中的花,刚绽放绚烂就毫无踪影。对于冬天却发疯似的喜爱,并在心中封存了一份又一份类似决绝冷漠的自以为是。甚至还凭借着浅薄的人生阅历去妄言春日下的虚伪与邪恶。就像是来不及追上公车反而去讥讽行人,不曾用心观察处身环境,反而妄自菲薄地在他人的言语中沉沦。只不过到了今年,泥土中又钻出了新芽,又出现了去年与我绝缘的花红柳绿,我便又狂热地跟着众人上山春游入园赏花。镜子里的嘴角又变成上扬的弧线。
类似这样的毫无理由地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我几乎常常都有,那些反反复复的例子层出不穷。
然而在霜打的清晨我想起某个人,突然觉得一切都是命运的牌局,一切在里面打乱又组合,再次混乱后又组合成其它的形式,似乎与过往毫不相关而又那么相似。不知最后是赢或否,自然也不知道某人在我心中也是如何的位置。
没有一件事是一定的,我们不可干预也不可怀疑这些事物是否会存在,甚至我们无法铭记,所以那些虫蛀般的表面华美的喜欢同样会毫无缘由地殆尽。
可我一直认为思想是短暂盲目的麻醉剂。
信誓旦旦地表明恨透了某某某,神态自若地宣告某某某不懂人情或不长脑子。每次反悔便当什么事情也不曾有过,像无忧虑地把烦恼悔恨如磐石般扔出去,也不管身后早已被砸得凹凸不平。人的一生不能有太多悔恨,毕竟没有那么多时间等待挽回。
说起父母,很自然地想到他们的啰嗦与多虑,也很自然地看见子女桀骜而又不屑的神情。然而如今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一句句貌似庸俗重复而又没有架子的话,是用真理在支撑。不可抗拒的压迫力,致使在过往的抨击下仍然伫立在一代又一代的情感中。即便我如今明了,但若退至幼年,我仍然会选择这条路——抵触反对他们的路,这不是思想的片刻麻木而是人人都会尝试的心路历程,甚至这是既定的规律,这种规律,同样也是在几年后像我这样的时候,懂得他们并依赖他们守护他们的规律。这些规律经久不衰地缠绕,绕成只有过往才可解开的结。
几年以前我还无比热衷地追求玩具。那些小小的东西记录着我的成长,以及难以阐述的不解——类似于小弟弟小妹妹玩玩具时放光的双眸和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