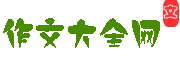(一)
他在那株榕树下停了脚,漫天的雾气终年不散,在湿热热的空气里沉沉浮浮,连那榕花开的都素,不着寸色,唯他手撑了一把青蓝色的伞。
脚下是一片隆起的小土坡,在铅灰色的水泥楼房之间显得突兀却尤其可爱,他倚着身旁苍老蓊郁、却挺拔的好像边疆卫兵一样的不死树,用手轻轻刮落那些干裂的树皮。那双黑的没有什么情绪的眼睛仿佛被染上一层柔和的光彩,竟微微有些神采。
“真是离开了太久了啊。”半响,他这样说道,好像怕惊扰了这片净土似的,轻轻地放低了声音。
他叫陆海西,陆地的陆,海洋的海,很美好的字眼,静静藏在看不出心思的瞳孔后面,如同心脏躺在胸腔里噗噗跳动一样融化在那一片温柔的幽水中。他爱这个名字亦爱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美丽——海西。
(二)
陆海西是天地的孩子。
正如天的高远地的广袤,陆海西从小就是一副不拘的性格,但真正下定决心的事情,八匹马都拉不回来。虽说经过几年在外的闯荡磨练,当年的孩子气已渐渐消退,但一条路走到黑的性子却是很难改变的。现在正值他事业的顶峰时期,本应是忙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抽不出来,但他却执意要回来——回到这个他呆了十几年的地方。在他被世俗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心脏深处,还存在着一丝不同的东西,在黑暗里慢慢拓出白光。
他满足的闭上眼睛,向着天空伸出手。好像触碰到了久逢的光亮一般,心里的空缺也被愈渐充实地填满。他有些高兴,不知是想起了什么,脸颊上浮出了两片红,于是摘下榕树枝上挂着的一片绿叶,放在嘴边,吹成单调淳朴的小曲,从皓白的唇齿间露出,然后随着晨风飞出了榕树广阔绿荫遮蔽着的地面。
他想起了这里原先只是一个横卧在山沟里的村庄,那时还没有这些高高的楼房,有的是一大片广袤的田地,金色的麦浪在田间翻滚,乡亲们手拿皮鞭赶着毛驴,每个人的嘴角都是满满的微笑;他想起了村边的孩子们手拿着狗尾巴草到处嬉闹,大人们一边斥责一边端着饭碗在后面追,老榕树下睡的正香的大黄狗不知被什么搅醒,冲着天边“汪汪”的叫,惊得榕树上的小